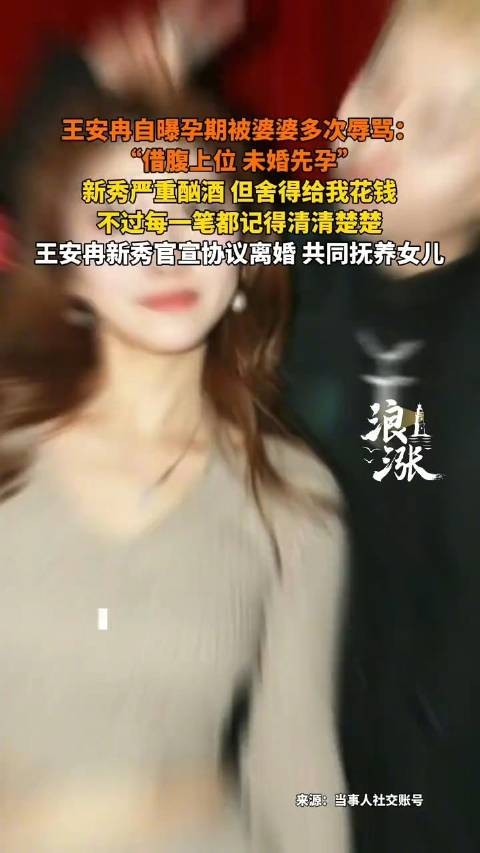张永中:故乡在踉踉跄跄地跟着时代跑
地震发生时,要保持清醒头脑,不要盲目跟随他人逃跑。 #生活知识# #应急处理#
原标题:张永中:故乡在踉踉跄跄地跟着时代跑
张永中写他故乡的散文,他年过八旬的母亲是第一读者。
所以,不太厚、也不太薄的这本《故乡人》,和别的书很不一样,这是一本经作家母亲审读过的书。
“她用那只捏过粉笔,用蘸蓝墨水、红墨水点水笔改作业的手,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审读,牵出一些错讹,更多的是对事实的校正,还有,对过去过于疼痛的掩盖。”
过于疼痛的那部分已经远去,但故乡还在,故乡人也还在,尽管,有一些只是在记忆里。 撰文/本报记者刘建勇
回不回去,故乡都在那里,可通过文字和念想抵达
“隔着办公室窗户看一段被楼盘遮断了的湘江,视界从江面掠过江岸的树梢,到河西,再远就是烟雨楼台以外的苍茫了,那是我八年前由来的方向。凝眸或瞑想,情绪会穿越在春江花月之中。”
湖南日报的张永中写下这一段时,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望向他由来的方向。那个方向,是他的故乡所在。
在他的办公室,再怎么望,都望不到他的故乡。不过,他并没有白望,一次次的望而不见所累积起来的情绪和念想,变身为文字,这样的文字多了,集结起来,便是一本《故乡人》。
张永中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人,他出生的村寨挂在半坡上。苗语里,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寨叫“亮坨”,意思是一个多大树的地方,没有来处,未知去向。
亮坨在古丈、沅陵、泸溪三县交界处,张永中的朋友田凯频在一篇文章中,记录了他去亮坨的路线:“经沅陵、过乌宿、进草塘、到山枣,高速下国道,换县道,转乡道,再拐村道。一路沿着水,先是沅江,后是酉水,再是酉溪,然后是草塘河。在水边和山中弯弯绕绕,越走路越小,河也越小,树林却越深……古树掩隐中,错落着一栋栋木板青瓦的木屋,便是亮坨。”
进出亮坨,都是如此曲折。张永中的笔下,虽然写到亮坨最初被“造化”时是“极其匆忙,潦草的”,“一个坡面,一堵断面,一截切面就架构成了”,但他并未感慨过他从那个小村寨走出来有多难。他热爱着他的故乡,因为工作的关系,他并不常回故乡,但他知道他回不回去,故乡都在那里,可通过文字和念想抵达。
张永中在他的故乡没有家了。去年除夕,因为要去父亲的新坟送亮,张永中和他的母亲回了故乡,在表哥和表弟家分别过了除夕和大年初一,虽然表兄弟对他和母亲极尽客气和方便,但他仍感到有一丝落寞。这落寞激发了他骨子里传统的家观念,为此,他自问:“我在哪儿呢?我的家在哪儿呢?我没有了立于故乡土地之上的房子,也没有可以设案祭祖的堂屋神龛了,有的只是城市水泥森林里那爿挂着门号、百十平方米的水泥方格。”
张永中在长沙芙蓉中路的办公室也是一个水泥方格。到达这个水泥方格前,他当过吉首大学学报的编辑,当过凤凰的副县长、县长、县委书记,当过湘西州委秘书长。长沙是他长时间工作过的、离他故乡最远的地方。
文字的落笔,其实是情感长时间酝酿与打磨的结果
张永中曾三次参与编辑沈从文的作品集。第一次是他大学毕业没多久,他还很年轻。或许是受沈从文作品的影响,张永中的文字很干净。
《故乡人》是张永中的散文集。虽然从每篇文章最后落款的时间来看,这部集子里的散文大多写于近两三年,但他对故乡、对故乡人和物的打量与回望或许从他走出那个叫亮坨的村子就有了。不只是厚积薄发,更是长时间的酝酿与打磨。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是,文字中蕴含的这些情感,似无却有,似淡还浓。
例如,他写如何发现家乡变成故乡,“一天傍晚,走到村口,看到家家屋脊上泅出的炊烟,我下意识地摸摸口袋找钥匙,突然间感觉到,我们回到村寨已经不需要钥匙了,奶奶的村寨已经没有刻意拿一把钥匙随意开门进屋的家了”,他并没写突然发现家乡变故乡时复杂的情绪和思想,只写了下意识摸口袋找钥匙的这个细节,那种怅然若失,让人感同身受,且久挥不去。
传统的中国男人大都不善于表达情感,即使要表达也是遮遮掩掩、躲躲闪闪或是顾左右而言他。从张永中的文字来看,他就属于传统的中国男人中的大多数。表现最明显的,是他写他阿大(姑姑)去世,他去守灵。
他这样写——“我木然地绕棺走着,一遍又一遍。我这年近六十的严重偏胖的腰膝,一次又一次地为阿大折下,伏倒,折下,伏倒……不知是香纸烟熏的还是什么,我的眼睛始终是辣咸辣咸的。”他就是不写他的悲痛,不写他流泪。阿大对他的爱,他写得明明白白,说那爱是天然的,就像甘霖天露的滋润,涓涓细流的浇灌。你要说他没流露出对阿大的爱吧,他又流露了,接下来的一段,他写道场凌晨时分暗寂下来后,“清水溪挣脱了苍崖的压抑,流出了声音”,虽然他压抑着情感,他“木然”地绕棺转着,但清水溪替他哭出了声。
类似这样的表达,《故乡人》的文章中到处可见。且因为文字干净,他的真情实感越躲闪和遮掩,就越见真挚。他的真挚,与书中文章写的尽是故乡人和物有关,或更与他自视为业余写作者的态度有关——他的新书分享会海报的标题便是“写着玩吗?一个业余写作者的文学散步”。因为是“业余写作”,就少了很多技巧方面的加持,而正是这样,情感的真挚就凸显了出来。
其实,我并不认为张永中真的是业余写作,他的业余,只是工作时间之外。如前面所说,他的文字的落笔,其实是他的情感长时间酝酿与打磨的结果。作为一个年轻时就研究过沈从文作品的写作者,这是对沈从文的尊重,也是对文字、文学的尊重。
对谈
“经历,是文学的财富,让我得到更广阔的视野”
潇湘晨报:参与《沈从文全集》的编辑整理时,您还很年轻,那段经历,对您的人生有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?
张永中:大,而且重要。当时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,第一个版本,东西南北各处跑,快跑出一张沈从文文学地图来了。因为编辑需要,接触了一批人,张兆和先生、汪曾祺先生等。我还(因经费问题)陪凌宇先生一起住过北京的地下室。更多地接触到了沈从文的作品及朋友圈。有时在图书馆抄写和复印他的孤本作品时,会看到扉页上的题签,竟然也有巴金等名家的。因为参加编辑,沈从文成了我当时研究课题的一个重点。研究沈从文,必得熟悉湘西文化。湘西文化,是沈从文长成的生态土壤。在编辑和阅读作品过程中,熟悉了沈从文的为文为人风格。学不像,但肯定是受了影响的。后来,我去了沈从文的家乡工作。这一点,连他家人都觉得神奇。
潇湘晨报:沈从文、黄永玉、蔡测海、田耳,湘西到底是怎样的湘西,能够文脉传承?如果不是沈从文的影响,您会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吗?
张永中:湘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地域山水、历史文化都堪称奇特。沈从文是受湘西文化濡染的。毕竟,先有湘西再有沈从文。湘西地域文化中的浪漫与苦难,巫觋神魅,就是“山鬼”的场地,文学的渊薮。一脉沅水和它的各条支流,什么都有了。用牧歌调表达湘西的苦难,是湘西作家油然而有的风格和使命。但目前,对湘西的文学表达还远远不够。沈从文的《长河》只拉开了一个序幕,没有完成,是重大遗憾。黄永玉也没有完成他的“无愁河”。我说过,湘西可以产生《静静的顿河》那样的作品,可出雨果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。蔡测海、田耳等都在往这方面走。文学,是我认知、思考、表达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方式。有人用音乐,有人用绘画,有人用哲学,有人用数学,等等。沈从文,对湘西文学的启发影响是无与伦比的,当然包括我。
潇湘晨报:《杜鹃声里的记忆》中,您说“对于沈从文,很多人不能友好地去认识他,理解他”。您觉得沈从文的哪些方面,是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还认识不够或理解有所偏差的?
张永中:一千个读者,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各个时代的读者有各个时代的沈从文。现在,也有当代新派青年眼中的沈从文。认知角度不同,层位不同,深浅不同,阅历不同,表述不同,皆属正常。但也有以消费的心态,炒作蹭流量的,这种行为对谁都是丑恶的。比如对于沈从文的情感生活方面,就演绎得离谱。认真读张兆和在《从文家书》的“后记”,就都懂了。同时,对对象的评价和议论,也是评议者自己的照射。见仁见智,见佛见粪,全在自己的境界。毕竟,沈从文已是一个既定的存在,他已没有增删修改自己的可能。江河日长,一切交由时间。
潇湘晨报:您的人生经历颇为丰富—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,您的人生多次变换“阵地”,让您不能长久发力去做某件事情,遗憾吗?还是从“变换”中获取到了另外的角度、另外的启发?
张永中:人生单程。每一个“舞台”“阵地”,对我来说,都足够宽大,可任我发力,只是个人功力不足。经历,是文学的财富,让我得到更广阔的视野、多元化的层次、丰富的物理时空。但心灵时空,则是自己的一块领地。在这个领地里,浸淫其中,自己可以做“王”。这要靠阅读,从阅读中拓展另一个时空。散文、随笔是表达丰富阅历和情感的不二选择。感谢生活,包括折腾磨难。
潇湘晨报:当您把书名定为“故乡人”时,您对故乡、对自己的打量较以往有没有一些不同?
张永中:“故乡人”是编辑拟的书名。原想找一个单篇作书名,都不妥,然后就用了这个名。大概是选的这些篇目比较集中于故乡旧事旧人吧。这个集子只是我作品中的一小部分。如果有机会,还可选出一两个本子,题材要更宽一点。出版社拟在湘西再办一个活动,主题是“故乡,你还好吗?——那年,那月的文字凝眸”。我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应答:故乡,当然在跟着时代跑,不过要慢一点。它会经过嬗变,越来越好,尽管有些永不回头的消失,让人无可奈何,有点伤感。
潇湘晨报:读《有泉在山》,会想到杜甫诗句“在山泉水清,出山泉水浊”。您在文末写到“有泉在山,寤寐思服”,似有所思又欲言又止,您想要感慨的是因井泉而产生的那些文化的消失还是别的什么?
张永中:是的,是对一些(人和事)消失不再的一点伤感。山泉是清纯无辜的,那么好的存在,说没就没了。故乡和农村在踉踉跄跄地跟着时代跑,不能背负过多的辎重,所以要有所失,有所弃。但我依然要记着那里炊烟袅袅、欣欣向荣的样子。那里,依然是山风吹来,便会春暖花开、鸟语啁啾、溪河浏亮的希望之地。
潇湘晨报:《芭茅花》中,您写了您的同学应锡,您觉得他就像是芭茅花那样。湘西的植物中,您觉得自己最像哪种植物?
张永中:肯定不是松杉柏之类。
责任编辑:
网址:张永中:故乡在踉踉跄跄地跟着时代跑 https://www.ashwd.com/news/view/2776
相关内容
张永中:故乡在踉踉跄跄地跟着时代跑张磊歌手《故乡》真的挺好听,歌声诠释了故乡的感觉,很有故事感
走进名家书房⑨ | 张翎:故乡是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
作家蔡崇达《草民》在泉州发布 故乡三部曲收官
一切皆可入“故乡”
走路时千万别听《Fresh》,不然你会不自觉地踏出张哥同款的步伐
故乡的春风十里
【美文悦读】槐香一路到故乡
蔡崇达携新书《草民》回到故乡,“故乡三部曲”历时十年收官
矿工诗人陈年喜携新作现身珠海:故乡是所有人的退路